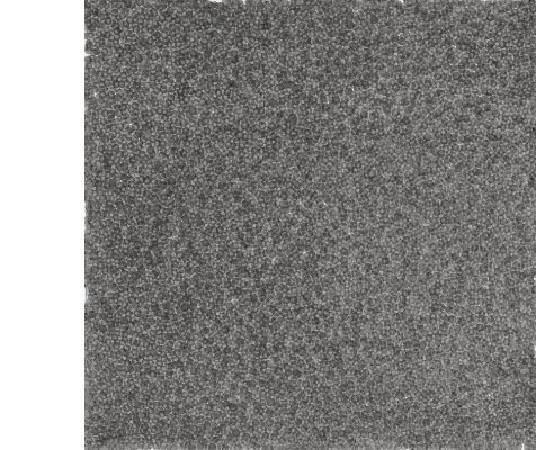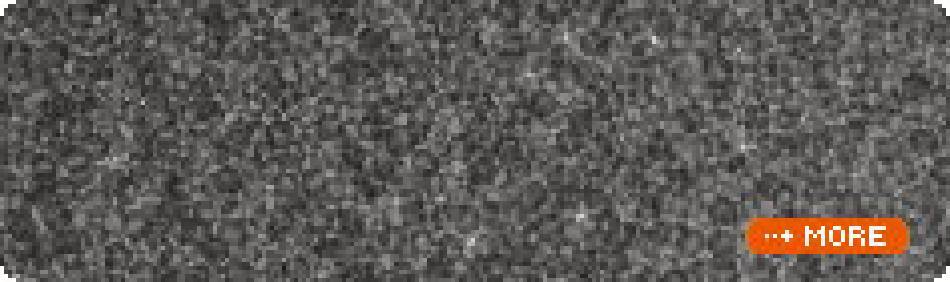2009-06-18|撰文者:王嘉驥
張羽(1959-)是中國大陸自1990年代以來「當代實驗水墨」的核心人物──既是理論的號手,更是創作的實踐者。以「實驗」作為一種前衛的手段,張羽在晚近的一篇文章當中,指出實驗水墨在語言的建構上,開創了兩種新的表現:其一,「非具象的圖式」;其二,「痕跡圖像」。(註1) 放在張羽個人的創作脈絡來看,屬於非具象的圖式呈現,主要以他的《靈光》系列作為代表,此一系列自1994年開始發展,於1998年達於高峰;痕跡圖像則以《指印》系列為代表,最早可以回溯至1991年的首次嘗試,而後在擱置十年之後,從2001年開始,才又重拾此一形式實驗,並發展至今。(註2)
就以《靈光》系列而論,張羽試圖回歸他所自言的「水墨的單純和本源性」。(註3)在媒材的運用上,只使用宣紙和水墨,工具則是毛筆。在創作的過程中,根據張羽的說法,「始終保持著墨色的豐富性和細微的水墨性變化」,而且試圖「控制住整個畫面的空間關係」。(註4)《靈光》系列以反複的運筆皴擦作為積墨的手段,蓄意營造「筆墨在宣紙上的運行痕跡」效果。(註5)「殘圓」與「破方」不但是張羽有意經營的語言符號,更成為《靈光》系列慣見的副標題。就創作的意識而論,圓與方的思惟仍舊延續了中國傳統哲學的宇宙觀,試圖從中開啟具有現代意義的感性空間。
以中國傳統陰陽二元論的觀點,在圓方的語法結構之中,嘗試走出一條現代化的道路,藉以作為抗衡西方抽象藝術的東方手段,此一做法早在台灣1950年代末期以至60年代期間,已有「五月畫會」和「東方畫會」的一些藝術家嘗試過,最知名者譬如:陳庭詩(1915-2002)、劉國松(1932-)、李錫奇(1938-)等人。不但如此,圓方結構作為中國或乃至於泛化的東方符號的感性運用,即使到了今日,也仍然是許多標榜「現代水墨」的台灣藝術家的方便話語。相較之下,張羽《靈光》系列作為1990年代中國當代實驗水墨的重要嘗試,必須放在中國大陸藝術發展的脈絡來看,方能見出其意義之所在。
實驗水墨於1990年代在中國大陸的崛起,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自1950年代以來對其他藝術表現的壓抑。抽象藝術在1980年代之前的中國缺席,主要受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箝制,而成為一種禁忌。再者,黑山黑水作為水墨形式的表達,也在文革之初,隨著林風眠(1900-1991)所遭受的整肅與迫害,而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犯罪。就以此論,中國當代實驗水墨對於抽象形式的嘗試,或乃至於繪畫本質的辯證,遲至1990年代方纔展開,似乎亦可視為「現代性」(modernity)的一種延遲。
雖然是從當代的立足點出發,張羽以「靈光」作為主題的命名,輔以「殘圓」與「破方」作為子題,其情感的意圖仍然維繫著傳統如何轉化的議題。在美學的視野上,他對於水墨的精神性如何顯現,也具有高度的「現代性」自覺。殘圓與破方不但具有文學性,同時也是對於傳統水墨繪畫的反省。在視覺的呈現上,《靈光》系列創造了幽深的神秘空間,雖如張羽所言,屬於非具象的「圖式」,卻仍自成寰宇,而且引人虛空中的廢墟聯想。張羽曾在1998年指出,《靈光》系列運用了「寫畫」的概念,不過,他所形塑的畫面卻與「書寫」較無關係,而屬於意象式的造境。對於媒材的運用,《靈光》系列主要以積墨的方式構成畫面。利用筆墨重疊反覆的皴擦、堆積,乃至於噴染技巧,最終使「殘圓」和「破方」的意象在宣紙上形塑為一種由墨團所構成的具有物性聯想的量塊空間。
如果說《靈光》系列的創作意識,主要仍以中國繪畫所引以為傲的「筆墨」傳統,作為其主要的對話對象,《指印》系列應可視為張羽更具前衛態度的藝術實驗。在《指印》系列當中,張羽捨棄了以筆就墨的傳統作畫形式,改以右手食指蘸墨、蘸色,甚至只蘸泉水或清水,直接在宣紙上形成印壓的痕跡,藉以作為畫面構成的最基本造型元素。
以指頭或手直接作畫,雖不是中國繪畫的常態,不過,自古以來卻也時有所聞;因此,很難稱得上是新鮮事。清代乾隆時期的畫家暨論者方薰(1736-1799),更曾在其所著的《山靜居畫論》述及「指頭畫」在中國的歷史。方薰不但將「指頭畫」的源流溯及唐代的張璪(活躍於八世紀後期),同時也記錄了明代以指頭作畫的名家,包括吳偉(1459-1508)和汪肇(約活躍於十六世紀前期)。(註6) 清代以降,畫史上最富盛名的指頭畫家,則非高其佩(1660-1734)莫屬。到了二十世紀,大師級的畫家潘天壽(1897-1971)也曾以指頭作畫見長。
儘管上述畫家都因指畫的特殊才藝而傳為美談,放在傳統畫史的脈絡之中,以指頭、指甲或手作畫,並不屬於正統筆墨之列。換言之,傳統的指頭畫所追求的,主要是另類的筆墨趣味。就以筆墨而論,傳統畫家以指頭就墨,雖然捨棄了用筆的「骨法」力度,但仍舊重視水墨在紙絹上流動所致的韻味。方薰在論「指頭畫」時,其修辭強調畫家以此技法所創造出來的「淋漓恣意」;(註7)張庚(1685-1760)在《國朝畫徵錄》中描述高其佩晚年的「指頭畫」時,更以「指墨」來彰顯其韻味之所由,並以「便於揮灑」之說,來強調「指頭畫」的特性。(註8)無論是「淋漓恣意」或是「便於揮灑」,都指出了畫家選擇以指頭作畫的審美思量。由此也可看出,傳統指畫的旨趣,主要還是以服務中國固有的形象暨美學體制,作為其視覺形式的根柢。
張羽以「指印」所進行的創作實驗,明顯不同於既有的指畫傳統。他將「指法」設定為以指含墨或含水,而後在宣紙上進行一系列的印壓動作。雖然張羽在自述當中,將《指印》定位為一種「痕跡圖像」的營造,他實際所完成的作品卻不容易用「圖像」的概念來加以理解。他以指壓所構成的畫面,並沒有形成任何可供聯想的形象「彷彿感」。若要從「圖像」的觀點來討論,《指印》算是不折不扣的抽象構成,而且與現實世界的物象指涉、簡化或概念化無關。
《指印》既是印壓動作的行使,看似帶有「行為」(performance)的意識與特質。不過,「行為」本身屬於「演出」的概念,張羽的《指印》卻又強調印壓在宣紙上所留下的「痕跡」結果。就此而論,《指印》作為物質性的痕跡記錄,最終還是指向一種「作畫」的概念,而與「行為藝術」(performance art)意圖賦予「行為」自身的意義,還是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張羽在關於《指印》的創作自述當中,特別指出「指印」作為「與身體有關的行為方式」,乃是與傳統中國社會的「契約」形式息息相關。(註9)其實,應該更準確地說,就「契約」而言,「指印」的行使意味著身分的確認與印證,一如今日世界將「指紋」視為驗證「身分」的圖徵。既然涉及身分的指認,指印作為筆墨的替代,同時也是一種「主體性」(subjectivity)的宣示。就其意義而論,指印成為張羽的刻意選擇,亦是針對傳統繪畫的筆墨體制,所進行的一場反省與對話,而且是為了凸顯藝術家自身所處的當代位置與情境。
在形式的表現上,張羽對於指印的行使,與淋漓揮灑的墨韻寫意大相逕庭。他以極為內斂自持的指法,讓指尖的印痕以圓形呈現,並控制在極小的方寸之間。透過反覆印壓的過程,張羽以同樣的動作,構成了看似均質的抽象畫面。圓形的色點以各種可能的相對關係,有時互不交集,有時不均勻地疊壓,有時則以嚴格的章法,讓圓形的色點進行綿密的幾何交集。整體而言,張羽是將極小的造形予以極大化,使其佈滿畫面。
觸覺是張羽作品的另一特殊質地。就指尖與宣紙所形成的關係而言,均質控制的圓點屬於造形的意識,觸壓似乎更是《指印》創作的核心所在。指尖在紙上使力所留下的壓痕,形成一種觸跡。觸跡亦是心跡的顯現,《指印》系列也可理解為藝術家「心法」鍛鍊的集成。
相對於張羽為《靈光》系列所賦予的造境意識,《指印》系列則是反敘事,反抒情,而且反意境的。《指印》如果是心法的集合體,或是藝術家個人主體性的顯現,那麼,《指印》作為視覺的記錄,更多地流露了藝術家關於「我」的反覆交談或對話。更進一步說,每一次的觸跡都是「我」在當下的「念頭」顯形,而念頭來來去去,也都是「我」的分身。值得指出的是,在嚴謹的意志控制下,張羽的每一念頭都被馴化為均質的圓點。觸跡的深淺固有不同,圓點也各自和而不同,卻都反映了念頭的無窮反覆,才滅即生。若以此論,《指印》所涉及的心法,似乎與禪學的觀念不無關連。
張羽典型的《指印》作品,以圓點佈滿頗大的尺幅,而且經常沿用中國傳統繪畫習慣利用的卷軸形制。這些作品嘗試以單一造形元素的重複,意圖在沒有情節的單調之中,營造出以觸覺結合視覺的複雜感性,甚至走出耐人尋味的精神性。
美國的藝術史學者諾曼‧布萊森(Norman Bryson)在探討西方繪畫史中的「再現」(representational)傳統時,曾經以中國繪畫作為對比,指出中國繪畫對於筆墨的運用,具有一種「直證」或「直接顯出」(deictic)的特質。觀者得以在視覺上,透過畫家在紙絹上所留下的痕跡,回溯其創作的時間過程,彷彿見證了藝術家用筆或用墨的當下。(註10)對布萊森而言,在中國傳統的山水畫當中,山水固然是藝術家表現的「主體」(subject),筆墨(the work of the brush)作為藝術家身體的延伸,如何使觀者感覺如在現場同步觀看,亦即一種「即時」(real time)之感,同樣也是藝術家創作的「主體」之一。(註11)藉由筆墨的痕跡,觀者彷彿見證了藝術家在創作當下的身體勞動──對比於西方,布萊森認為此舉明顯具有「表演」(performing)藝術的特質。(註12)
張羽近日也將《指印》的創作過程,透過同步錄影的剪輯,並且加入配樂,製作成為影像的記錄。(註13)藉此影像記錄,觀者或許更能理解上述布萊森對於中國水墨繪畫所作的觀察與詮釋。指印雖不同於用筆,卻是更直接的身體運動。張羽以同步錄影的手段,確認了《指印》也有發展為一種儀式性的「演出」可能。然而,同樣值得指出的是,《指印》作為一種時間的藝術,最終所完成的「畫面」,卻反而失去了時間的線性。除非透過錄像的記錄,或是在現場見證其演出,否則,《指印》一旦完成為畫面,觀者再也無法回溯指印烙痕的先後。即便是藝術家本人,至多只能記得佈局的先後,同樣不可能在每一個印觸的痕跡之間,如實地分辨出每一手的明確次第。
《指印》是關於時間的累積或甚至疊壓。藝術家的每一手印觸,亦猶如圍棋棋士所下的每一子。所不同的是,張羽所面對的是一面全無經緯的空白,而且,在空白的畫面之前,藝術家面對的只有自己,既無棋局的規矩限制,也無敵我分明的黑白對戰問題。更進一步說,「指印」作為書寫的媒介,張羽所面對的其實是藝術家渾然的自我。眼前的一片空白,究竟將會成為倫理秩序的反映,或是個人內心倉皇失序的映照,或甚至是一場全面的交戰,致使最終一切淪為廢墟的心理投射?張羽的《指印》是某個時間段落的總和體,雖然不是現實世界的具體再現,卻也因為是藝術家內心的直證,而展現了複雜的心境起伏或心理狀態的發展及變化。
《指印》從張羽個人心內的方寸出發,其所完成的畫面,雖然抽象,而且滿佈私密的心理符碼,卻都是關於藝術家個人與現象世界的對話。
註1:張羽,〈張羽:水墨,水墨,是一種精神──當代實驗水墨的藝術史意義及其語言特徵〉,收錄於《張羽:一個當代藝術家的個案研究》,殷雙喜主編(湖南:湖南美術出版社,2008),頁20-21。
註2:同上註。
註3:張羽,〈自述〉,收錄於《張羽:一個當代藝術家的個案研究》,同註1,頁146。
註4:同上註。
註5:同上註。
註6:方薰,《山靜居畫論》卷下,收錄於《畫論叢刊》(下)(台北:華正書局,1984),頁453。
註7:同上註。
註8:張庚,《國朝畫徵錄》卷下,收錄於《畫史叢書》(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頁1309。
註9:張羽,〈我說「指印」〉,收錄於《張羽:一個當代藝術家的個案研究》,同註1,頁234。
註10:Norman Bryson, Vision and Painting: The Logic of the Gaz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89-92.
註11:Ibid., p. 89-90.
註12:Ibid., p. 92.
註13:參閱張羽於2007年10月1日至22日期間,同樣以《指印》命名的創作記錄,全作剪輯為31分08秒的影片。
REACTIONS
0
0
0
0
1
熱門新聞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