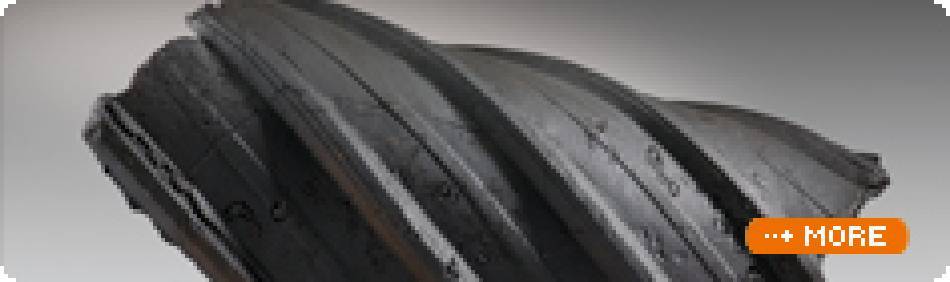2011-01-25|撰文者:王品驊
在他的作品中,我們看到當代生活失去的故土。
倘若我們試圖去思考台灣當代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或許這樣的社會性回顧,會讓我們很自然的將關注焦點,放在戰後農業與建築業的影響,在國家與公共政策主導下,這兩個層面確實是改變了台灣地貌最多的領域。走向荒蕪的農業和興盛的建築業,一消一長之間其實正是土地異化的過程。
《非器》系列是邱梁城首次正式發表的大型陶作系列。在他工作的地方,觀者可以看到有些剛完成土塑、待乾的作品,以及ㄧ些已經經過窯燒階段,在火的煅燒之後成為堅實陶體的作品。倘若仔細檢視邱梁城的創作發展,觀者應該會發現今年(2010年)這些新作系列《非器》,不僅僅是他創作歷程新的階段之體現,更進一步可以發現這個階段也同時是多個面向的交匯點。第一個層面,是具體而微地體現著某些台灣戰後社會文化片段卻關鍵的縮影,第二個層面,則是逼顯著其個人的存在處境。而這兩個層面,事實上都能夠從《非器》系列的觀念表達,以及所運用的媒材「土」來進一步討論。
【從當下時間到多重時間的想像】
遠遠望過去,《非器》系列編號1,像是一件大型站立著的某種殘片。近看發現物件是燒鍊後的陶體,並且在不規則邊緣的捲曲形態中,開敞出內部既切割又組合的建築性架構;觀者順著物件本身的曲線轉到陶體後方,發現整個物件是被人工化線性疊加的外圍結構所組成;高溫燒成的圓弧性陶體,還呈現出金銅釉的金屬色感,使整個陶體前後有不同的造型語言,前方開敞空間的土版層次,和後方透露出歷史器物沈積歲月的質感、又有點像是在某個荒湮蔓草般的遺址空間出土的詭異生物蛹體,前後兩種特質相異成趣。同樣的人工化線性形象,也出現在《非器》系列編號2,只是這件碩大捲曲的螺紋陶片,不再帶有金屬光澤,卻如同不知名的生物蛹般橫躺著、從另一邊看,內部又像是個遠古螺貝的造型空間,可以順著貝殼般的圓形空間看到尾端的穿透性開口。
《非器》系列編號5,與前兩者相較之下,其形體更不規則地開裂,使得在前兩件作品在胚體上存在的人工痕跡和自然裂紋之間的反差更為突顯,同時因為物件較小,觀者同時即接收到圓弧胚體,內外兩種既像是人工建物結構、又像某種器物般的圖紋之間不斷銜接與翻轉。《非器》系列編號3,整個形態則又像瓦片結構、又像金屬巨人斷裂的怪手。特別的是,在前述幾件中維持著力量綿延的長條曲線,到了這件作品,卻以拉直曲線、轉折、中斷來表現。
倘若我們用一般的審美思維來觀看這些作品,我們會發現這個系列有些難以立即論斷的特徵。例如,一眼望過去,這些作品或站立或躺臥,有些捲曲的形象看來像是具有生物性的蛹、或因為有著堅實斷裂的缺口而像是某種大型機具的零件、更有些則像是建築的殘片、甚至像是時間流逝久遠後的遺址碎片,這些作品顯然都不傾向於表現某種完整的形象,反而相較之下,更像是對於某種流變形象的瞬間掌握,不僅所呈現的物件形態,像是某種更大力量的局部體現,仔細思考在充滿生物和人工遺跡之間的變幻性,更讓作品是處於多重歷史時空和時間經驗中。整個系列,都像是刻意捕捉著各種狀態上的不確定性,或是彷彿會持續在多種形象之間變易著。
但是從每件作品最後呈現為陶體的冷硬質感來看,前述特質又讓觀者感受到那些作品仍舊體現著,某種正在進行中的當下時間。土塑形過程,具有延展性的胚土透過那些線性、弧形曲線,展延著內在力量與時間連續性,如同一種軟性的視覺表達語言(特別是在尚未窯燒的待乾胚體上可以感受到);在經過窯燒後,卻轉化為堅實陶體,時間像是被那些金屬光澤、紅磚陶或是沈穩礦石般的質感和體態所凝結。
正在進行中、未完成性,構成了這個系列,十分特殊的形象表現特徵。就像是某種更大、超然力量的瞬間力道,被局部的框取為每件作品的個別樣態。《非器》系列的獨特之處,顯然是由單件作品之間產生了多樣化、系列化關係來表現,這種創作構思,恐怕不再是運用單件作品體現個別完整造型的手法來發展了,似乎創作者更重視的作品與作品之間的對話關係和差異,因此,觀者將發現這些系列作品其實構成了一個豐沛、多重想像的「場域」—那是讓觀者得以在作品和作品之間持續發現的相近關係和差異形象,讓觀者的想像,具有可不斷擴充、往返、相互補充的整體空間。
《非器》系列如此看來,還有一個特徵,無論是從單物件,或是整體來看,都具有一種「非語言」可捕捉的特徵,其形象在各種斷片、重組之中變異著,各種細節會聯繫出人類文明的某些片段想像,但幾乎都無法定位捕捉,甚至以筆者的個人觀點來說,正是這些作品所呈現的「非語言性」,使得這些作品看起來仍處於一種尚待解讀、以及仍會持續發展的狀態,並且試圖從某些歷史視點或固定語言的描述中脫逃。
【現代性生活的人工化與自然之間】
何謂正在進行中的「非語言性」呢?當代藝術所關注的問題,是什麼呢?倘若以現代城市的理念來說,二十世紀初人們對於現代化生活的樂觀與追求,造就了現代建築以簡潔造型、講求功能性之直接表達的視覺語言,同時也追求著某種穩固結構的、具有本質象徵性的、永恆時間的詮釋?但曾幾何時,二次戰後,代表著人類擴張野心的現代社會與經濟策略,的確在講求效率的專業分工和技術追求之後,使得地球整體處於二十世紀末的過度開發的危機之中。當代藝術在反思現代社會過度擴張的生態浩劫之後,重新尋求各種未來的生存之道。看來這些《非器》系列,正有著要從穩固結構和永恆象徵的束縛中脫逃的意圖呢,在此系列的作品之間,彷彿藉著相互間的差異、對比,以及瞬間即逝的當下時間,重新思考藝術。為何這些作品會具有這樣的特質呢?而且筆者認為要討論這個問題,必須要從這些作品最基本的問題開始思考。
首先,透過創作者的訪談,觀者會理解到,這個系列的「成型」方式,是經由土版在人工建材的波浪板上壓塑而來,藉此成形的土版又在從模板上取下時,經由各種力量的拉扯、扭轉、變形,塑造出既帶有力量發展、又帶有黏土延展性的多種形態。為何要採取這樣的成形方法呢?創作者說,這些構成方式來自於持續思考著人造物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他曾經實驗過多種手法,運用各種生活中的現成物、工業大量生產品來作為塑形的容器,運用土、水、擠壓、重量、乾溼變化、時間等等因素,觀察和思考「土」和這些造型語言之間的關係。在這樣過程中,「土」作為一種引導思考的媒介,不斷跟各種造型語言和力量關係進行對話。
也就是說,《非器》所關注的已經不單單是造型的純粹審美形式,而是從杜象(Marcel Duchamp)的《噴泉》之後,所衍生的現成物和觀念性問題。也如同1960年代安迪渥荷(Andy Warhol)將超級市場的湯罐頭箱子,移置到展覽場所引發的提問,倘若藝術取用、挪用了現成物的形象或視覺符號,那麼藝術究竟要表達什麼樣的問題。觀者應留意《非器》雖然取用了工業生產的現代性建材,但首先,此種建材通常運用於各種工廠、臨時搭建的空間、甚至違建的功能性,反應著台灣特殊在地化之後的社會經濟與城市文化背景。其次,在創作者的運用中,僅僅取用其作為人工造型的憑藉,並未挪用、再現其整體的文化符號的象徵性,因此,如果觀者未經細察,一時還未必能辨識出該視覺語言取材自該特定建材。也就是說,創作者迴避了太快經由符號再現而解讀出議題性的創作策略。
觀者尚須留意,不僅僅是人工物象的取用態度之謹慎,同時「土」在此也已經不單單只是視覺藝術的一種媒材類型。而是藉著銜接視覺表現語彙與現成物背後的社會性語言體系,在兩者間產生了新的對話和關係。也就是說,「土」在此尚包含著社會性、以及創作者個人存在的複雜體驗成份。
【碎裂的象徵性時間 人與土地的疏離流徙】
出生於1960年代、成長於嘉義的創作者,過去還有許多的風景素描和攝影,在那些風景的掠影中,總是像隱藏著某些難言的片段。針對此種可能性,創作者提到許多成長過程關於農村的記憶,像是農田收割後將稻穀鋪曬在大馬路邊,小孩就像是移動式稻草人般的坐在路旁看顧著穀物。秋收時節的清晨,天色仍暗有時就會有不知從哪個村莊的農家,趕著鴨群去剛收割過的田野吃剩餘的穀子。這些是1970年代中期之間的景像,到了1970中期之後,家中、村子裡許多農戶都陸續將農田改成魚塭,改作養殖魚蝦的生計。以靠天吃飯為主的鄉村生活方式,在進入1980年代的過程中,也邁入了開發道路、拆除祖屋的轉變,農漁生活早已不足以支應生活開銷、子女教育等經濟需求,年輕人紛紛離鄉,大量外移人口集聚在都會中。
也就是說,雖然還有著關於農村生活的片段印象,但是實質而言,在這些1960年代之後的世代所親身經歷的可見過程,尚不足以說明在上述表象之下的農村真相,台灣許多地方的農村土地只是一步步邁向了棄耕與荒蕪。事實上台灣的農業政策早已藉由三七五減租的過程,一方面是讓佃農獲得田地,另一方面,實則是引導地主在販賣田地後,將資金投資工商業發展,因此,1960年代雖然仍存留農業生活的根基,但事實上農村已經在政府更為鼓勵工商業發展的社會經濟步調中日趨衰敗,農村人口大量外移,許多應就學的年輕女性,往往因順從家中農獲不足的經濟需求而進入了工廠,進入了長時間工作的生產線,成就了1980年代以後台灣以加工出口為大宗的經濟起飛的美名。
因而當代時間之下,似乎總是伏流著不斷變異著的歷史時間,戰後出生的世代、直到1960年代,在大學教育之前,閱讀的都是中國歷史,藉著解嚴前後的政治震盪,才翻開了台灣在地歷史迄今仍掩埋斷續的片段。倘若法國精神分析學家拉岡 (Jacques Marie-Emile Lacan)的觀點沒錯,那麼成長於不明的歷史與當下認知中的世代,不僅在「鏡像」階段(mirror stage)的自我「想像」(the imaginary)層充滿了外來眼光的注視 ,同時在社會符號、語言結構為基礎的「象徵」(the symbolic)層也充滿了政治挾持下的語言鬥爭,無論是台語、國語、客語,都在語言體系本身的權力角逐間,成為浮動、破碎、難以明確指涉的狀態。因而,即使在政治角力的競爭中,解嚴前後激起了「台灣主體」、「本土」的集體意識,然而這些作為標籤般流動的符號,只能更對應出個體與當下生存真實間的疏離和碎裂性。
社會語言體系的鬥爭與失去真實的憑據,同樣的會循環反覆在戰後藝術教育、創作、評論語言體系的混亂中。戰後的藝術教育對於藝術的詮釋、媒材分類、風格流派、專用術語,體現出發源於西方的不同影響源,卻同時以脫離文化脈絡、生活關連性、理論概念的前後對話關係而如同「惡性場所」 般的並置和混用於台灣的文化場景中。
筆者即曾經在探討創作者2005年迄今的繪畫系列時,在文章中提到創作者作為出生於農村,卻留在台北都會成為專業社會的文化移民者,具有一種「游離土地者」或「居無定所者」的狀態。當時這樣的探討,即出自其繪畫系列中所表現的對於都會生活的反省。但事實上,這樣的生活反思與個人生命的追溯,在《非器》系列直接以「土」作為創作思維的媒介時,更深一層地透露出那種「游離土地」和「居無定所」的斷裂感,並非全然由移居都會而來,而是從出生之始,台灣農村的實質存在性,就已經隨著農業無法維生的現實而瀕於被逐步剝離生命力的荒廢狀態中。
因此,創作者所運用的「土」,已經不只是一種限定性的創作分類下的媒材。這樣的創作思維,實則是延續著2005年迄今的繪畫系列。
【個體與社會之間 共振體驗、生存反思】
觀者在此若借助另一種解讀策略,回到他的創作歷程,是否更能印證他的創作思維所關注的問題。
《城市飛行》(2005~2010)是以平面數位圖像為表現的創作系列,由此系列又衍生了《城市變異.時空飛行》(2005~2007)油畫系列,從《城市飛行》系列運用數位製圖工具的最簡功能變造弧線、曲線的透視與穿梭空間,以重構出當時兩個創作系列中獨特的「對自然的轉譯」和「想像中的風景」的繪畫手法,深深體現出當時從數位圖像回歸油畫觸覺表現的繪畫歷程,其創作的根本動力來自於都會生活的反思,以及回顧了他自身成長背景中人與土地的關係。
從2005年至2008年他埋首於繪畫的方式,從畫面的表達來看,視覺語彙的表現問題僅只是他對自然轉譯和創造想像風景之過程中的一種需求,更重要體現在他創作系列間的關係,其實已經反應出他對於所處的都會生活的反省,和對於人與土地關係的重新思考。後述的兩項因素,我們在《非器》系列的發展之後,發現創作者是藉由繪畫系列,提出了人與土地的疏離,再透過了《非器》系列,回歸到「土」作了更往下的追溯,從這種反省和追溯體現出的,正是其創作思維的持續關注所在。
因而《非器》系列,首先是創作者回到了「土」作為媒材的這個起點。觀者在工作室看到那些待燒的土塑胚體上,彷彿就是閱讀到了這樣一種回歸土的創作需求,為了回歸「土」這樣一種能夠回應成長記憶的單純屬性。倘若觀者在此與之繪畫系列進行比較,從「土」開始的新起點,首先是揮別了創作者在繪畫中最為擅長的強烈色彩和空間層次的構圖能力,創作上將突顯出雕塑物件的造型語言、立體物的空間性、土塑過程力量的運動以及窯燒過程的釉藥和火的煅燒轉變,因此前述討論《非器》系列時,前述問題都逐一在其創作中成為表現的語言媒介。
創作者在那些待乾的土塑胚體上,其實還透露了重要的訊息,亦即當土版從建築波浪板上取下時,除了帶有波浪板的人工造型,同時還因此保留了土版在壓印過程中留下的最原始觸感,而這個粗獷的、近乎帶有繪畫性的「非繪畫」痕跡,恐怕正是創作者在重複的土胚實驗中所意圖捕捉的——能夠體現出在人為、人工性與自然性之間往返的不確定性。
我們可以發現,創作者將來自現成物的波浪造型轉用在各種可能性之間。也就是說,創作者似乎的確是透過此過程試驗著土的可塑性胚體,所能承載的自然延展性(例如力量的扭曲或自然斷裂的痕跡),以及由此所打開的人造物和自然物造型之間的關係。
對照於繪畫系列的「轉譯的自然」和「想像中的風景」,《非器》雖然回到了土的純樸屬性,但是顯然相對於創作者所置身的都會生活體驗來說,「土」已非「土」,「土」對於曾經有著漫長農業歷史與自然共存的人類文明血脈的當代人來說,還能夠讓人安身立命嗎?一種已經不能讓人安身立命的「土」,對當代人的存在處境來說,究竟成為了什麼呢?《非器》系列多件作品所透露出的人工與自然間的不確定性,能否回應這樣的生存體驗呢?
前述已經提及,從創作者並未讓現成物的語言以再現方式在作品中直接體現為一種文化符號,反而創作者是盡量將土塑、窯燒的純粹性力量仍舊保留著,因此,作品不僅未朝向現成物的再現式語言表現,反而讓作品朝向了各種形象與歷史時間的多重想像發展,例如前述所感受到的建築性、歷史遺址片段、或某種生物性。從單一作品創造出起點,聯繫著其他既有相似起點、卻也創造著差異的其他作品,在這種系列性、多樣化的關係中,創造出一個屬於他個人的創作的「場域」,其內涵就是透過盡量處於各種變形和不確定的時空指涉狀態,而讓創作朝向開放的想像,但同時又反映出了當代生活,對於人與生活關係、土地關係的反省。這種「非語言性」的造型取向,不僅決定了作品系列的非議題化,同時似乎為了更釋放出在隱藏於單純的「土」的追溯中,某種潛在於創作者個人、觀者之間、某種社會集體潛在的土地情感。
【從文化「失語」到「非語言性」的投注】
對於創作者來說,倘若環環相扣的藝術文化場域,呈現著藝術語言的混用和錯亂,如何能夠再回歸單純的人與藝術的關係之中?當台灣藝術領域的藝術概念都在鬥爭中,僅能成為各種外在性的指涉,無法觸及真實的感受,甚至語言的表達總是帶來誤解、帶離真實的可能範疇,創作反倒成為一種力圖逃逸於「藝術」之外的趨力。正是在層層的解離之後,讓觀者發現,創作者所重新觸及的「土」,再次展現著當代生活所失去的真實與不確定時間,而這種物質性的轉折,其實正是創作態度的重新拆解、重新質疑所帶來的力量。
藉著反思藝術語言的錯亂和都會生活對於真實的遮蔽,創作最後走向了在土塑的形體中,體現出素樸性張力之下的複雜性;以及經過窯燒、從土轉化為陶的過程,在材質屬性上表現出如同金屬、或瓦片、或礦石般的多重想像。陶作的製作過程,需要經過漫長的塑形、待乾、窯燒過程,窯燒過程一向還包含著相當程度的偶然性。相對於創作者的《城市飛行》系列的快速、穿梭的數位線性與空間切換,《非器》系列則顯現出了陶作製作更長時、精確、環環相扣的工作步驟,他從繪畫階段色彩飛躍、快筆寫意的工作狀態,轉入了需要沈靜身心全然投注的土塑窯燒,也的確在最後的陶作上呈現為更為單純內斂的表現語言。特別是這樣的一種吸引身心全然投入的工作方式,正是創作者曾經提及,試圖以此作為一種有別於消費社會、講求快速效率、忽略生活實指的另類存在空間,同時也是他認為真正能回到藝術與人的真實直接關係之所在。
從觀者角度來看,也因為這種長時投入的工作過程與態度,創作者幾乎是沈浸於像是召喚物質內在原生、純化力量的趨力中;《非器》系列因此表現了簡潔、動態的形象,作品細微轉折的語言,讓人感受到某種潛藏於塑形過程的時間刻劃、半溼半乾的土胚力量、或動態扭轉展延的「勢」等等,也同時提供給觀看著一種得以再度投注其間的機會。《非器》系列果然彰顯出在人為與自然的反思之間發生的「自然的轉譯」,一種不被「器用」的無功能性、以及「非語言」可定位的存在態度。
這讓人想起法國哲學家馬色爾(Gabriel Marcel)曾經說過:「個人與他的地方並沒有分別,他就是那個地方。」 當僅僅膠著於外來與在地衝突性的思考已經失去立足點,回到個人的生存真實,或許反而成為藝術提供反省力量、讓存在不再侷限於文化疆界、概念爭議的所在。
REACTIONS
0
0
0
0
0
熱門新聞
1